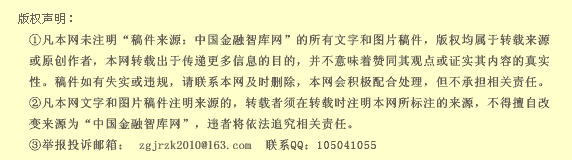顾雏军案件的尘埃落定牵起一桩15年前的历史旧案,虽然郎顾大战的硝烟已经消散,但认真回顾和思考历史或许可以让我们的未来不至于“欢喜得如此脆弱”。
王 安
中美贸易战,针对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川普政府精准打击,连排炮击。华为,以一己之力应对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及若干同盟者的全面围攻,真可谓凶多吉少,不死也得扒几层皮。女儿取保候审被扣在加拿大,川普政府已经而且还在组织更猛烈的炮火,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却表现出沉着、大气、睿智,令国内左中右们空前一致地佩服加赞许,纷纷表示一定要支持华为,虽然这种口号精神大于实质,也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
相比之下,那些中字头的电信企业,平日里享受着各种垄断性的资源和好处,却一丁点声音都听不见。有人惊呼,中国要是有一千个一万个任正非就好了。
面对这种呼声,有个人不知会做何感想。曾经的产能布局,心心念的冰箱大王之梦,15年前被戛然而止。面对能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任正非,顾雏军羡慕嫉妒的同时,是否会有些后悔?
如果当初不出事儿,在如今的贸易战中或许可以与任正非并肩,或可有些建树、青史留名。然而,关于15前那场“国退民进”之争和过去两年的“民退国进”之虞,只有在临界点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晰,亦或更有讨论的意义。 点名道姓炮轰老板 顾雏军怒告郎咸平
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一幕席卷全国的争论就此走向高潮。在此之前,郎批判的大名单上,已经赫然排列着德隆、海尔、TCL这些声名显赫的企业。
德隆曾号称中国第一民企,而出身国企的海尔和TCL以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旗手著称,在李东生八年磨一剑改制TCL之后,张瑞敏正力图分享海尔。而在郎咸平之前或同时,张五常、张化桥、梁定邦、史美伦都参与了内地事务。
这些香港人都曾负笈欧美,饱学西方自由经济的经典,他们一再让人们看到中国距离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直率地批评内地,掀起争论,而每一次争论都彰显了内地的进步与限度。 之前2004年1月6日,TCL集团整体上市,融资25亿元。4月6日,在海尔中建的公告中,一家名为海尔投资的企业浮出水面,它直接和间接地控制了海尔中建35.84%的股份。 7月31日,郎咸平直指海尔职工持股会,认为海尔此举是为了完成借壳和实现国有股权稀释。郎咸平指责顾雏军的罪名和张瑞敏、李东生同出一辙,即席卷国家财富。
曾几何时,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在中国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科龙、美菱、亚星客车、ST襄轴等4家上市公司相继被顾雏军纳入囊中。
郎说,顾雏军号称动用了41亿元收购资金,实际投入不过3亿元,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七板斧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 郎咸平带着7个学生,耗时3个月,每天只睡4小时做出了对格林柯尔的研究报告,他和学生共同署名。
对于郎咸平的攻击,张瑞敏和李东生几无反应。 8月26日,在香港发布TCL国际(01070.HK)中期业绩时,当被问到被郎威平质疑时,李东生神情淡然:“郎咸平是谁?”顾雏军却完全不刻意,8月17日,他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书,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 此前5天,郎咸平收到顾的律师函,主要内容如下:一、郎咸平需要详细书面汇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自己的演讲;二、如果媒体没有正确记录演讲内容,郎咸平需要向《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有关网站要求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三、给顾雏军一份演讲稿件,顾雏军要求郎咸平在8月16日以前完成第一、三项要求,在8月17日以前完成第二项要求,否则将会采取包括法律手段等一切必要的手段。
郎咸平马上召开记者会表示:一、绝对而且充分地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地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因此绝对不会要求媒体向顾雏军做任何形式的道歉;二、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演讲稿件,请顾雏军自己去找;三、绝对不接受律师函所表达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气。
挺郎扁郎阵营分明 张维迎周其仁挺身而出
一时间,内地经济学家集体短暂失语;几天后,两极分化。
一方面以“非主流”经济学家自居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中的赵晓、张文魁、张维迎、张军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
8月28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没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非主流”方面的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均到会发言挺郎,加上郎咸平本人的出色发言,会场几乎成了声讨“主流经济学”的场所。
经济学家攘攘矣,难得的些许碰撞,难得的零星火花。 在另外的场合,北京大学张维迎是最早出来表态扁郎的学者之一,他说:“有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10年国有企业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
张维迎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也就是良知,谁敢骂企业家或者政府就是有良知的。我也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
经济学家周其仁是另一个倒郎者看看郎咸平是怎样质疑的:“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就是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周其仁说:请问这叫什么研究态度?轻轻两个“如果”,就把问号变成了句号。所论问题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可以陷人入罪的侵吞国资!这让不明就里的善良人听来,怎不群情激愤?破绽在什么地方呢?破绽在于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企业,根本就不是国企。郎咸平连这个也没搞清楚,怎么就敢高调展开攻击?好比一位动物学家,用马的数据发现了关于马的伟大定理,然后大肆喧哗,人们围上来一看却是一匹鹿!
周其仁说:更叫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海尔公司发言人声明“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之后,这位大监管对自己指鹿为马的行径不但不感有一丝歉意,或多少觉得有点难为情,反而以攻为守,继续向海尔高调指控:“即使海尔是集体企业,它内部仍然存在两方面的利益代表,而海尔职工持股会的整个动作过程,恰好是一个将资产从青岛市向内部员工持股会转移的过程。”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算是一匹鹿,鹿也有鹿的问题”?!容我不依不饶问一句,你郎咸平先前关于海尔持股会侵吞国资的罪名,究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 扁郎派张文魁反对郎咸平观点,但他也表示,“至于学术问题,我对郎咸平在公司财务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尊重的,他的确在这方面有很深的研究。”
9月15日,上海财大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原副院长吴栋、上海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顾钰民等10位学者在上海声明挺郎我们对郎咸平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一、要分清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界限;二、郎咸平抨击西方产权理论和产权改革误区,反对把企业、金融和产业等方面存在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和以为转制为私有产权便可实现高效率这一流行做法,他的批评是及时和正确的;三、从我国现阶段实际出发,必须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发展的方针……
法学家群情激愤 道义责任还是法律义务
法学界也卷入这场争论。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认为:我们必须从中国20多年改革的整体视角来分析,这20年已经证明了以国企和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体现了全民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正是国企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实质性合法基础。
李曙光说:另外,我们要承认,中国法制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在转型期,很大程度上,一些稳定性、权威性很强的政策成为法律的代名词,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实践法”或者“政策法”。不能否认“政策法”是具有法律属性的,虽然它们离完善的“理想法”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李曙光说:正是这些“政策法”构成了国企改革的主要法律框架,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所取得的成绩,是在这样一个“政策法”的框架下面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国企改革和产权改革在形式上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
此前,有评论认为郎咸平诊对病但是开错药。北京大学法学院甘培忠教授表示,国有产权流失问题其实早已是一个社会共识,“但郎咸平关于维持国企布局不动,只要强化对经理人的诚信义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直接开办国有企业越少越好,国家在企业持股也是这样。”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鸿高没有完全抹杀郎咸平:我国大部分法律都是从“消防”的角度考虑急就而成的,自带“救火性”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郎咸平的炮轰迫使我们去考虑“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国企”,以及如何造就平等机会、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等问题。
上海交大法学院教授任荣明认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对经济问题发表个人见解,只要不是凭空臆造就无可非议。郎咸平的言语有些过激或尖锐,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学术需要民主,学术需要活跃,我们对不同的声音,不应苛求它表达的方式以及措词是否严谨。郎咸平确实不客气地指责了某些国企、上市公司,但国企与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公众企业,公众企业理应受到社会的关注。如果不同意郎先生的观点,可以反驳,公众也希望听到这些老总们的见解。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罗培新不同意任荣明的观点:的确,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小股东保护一直很成问题,郎教授的财务分析确实增大了真实信息的供应量,这正是社会所需要的。但另一方面,郎教授的推论逻辑极不严密,对法律更是缺乏必要的了解。任教授说我们不应苛求郎教授的表述方式及措词是否严谨,恰恰相反,对于已经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并且以学术操守自重的郎教授而言,坚持严谨的学术标准,是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否则将误导民众,严重的还会破坏政府决策。很可惜,郎教授这位公众知识分子,在应对媒体时有问必答,他的知识似乎没有边界,狂放到了极点,什么企业家就想着圈国家的钱,高管的信托责任是道义上的,不是制度上的,国企的保姆反而成为了主人……且不说国资流失这么个大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靠强化高管的信托责任来解决,至少郎教授不应当忽略我国《公司法》有相当多的法条要求高管必须忠实于企业,这种责任也绝不是什么道义责任,而是法律义务。
法学家真正以法理辨析的不多。复旦大学张军教授是经济学家,但他从更高层次思考问题:郎教授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从演讲的题目到内容已经有强烈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具有很强的超出学术讨论范畴之外的表述方式。 尽管有人贬低郎咸平的人品,但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近20万参与投票者中,90%挺郎,有人将他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国资委叫停MBO 分兵抽查国有股转让
当学者们轰轰烈烈打口水仗时,官员们不说话,坚决不说话。
官员最早回应是在2004年9月中旬,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小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操作过急,加之缺乏规范,确实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是当时国资监管机构还没有成立而且缺乏规范所致,但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与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相同,前途光明路径曲折,方向正确崴脚难免;另外就是这崴脚与我无关,当时还没我呢。
另一次回应是在9月29日,国资委研究室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国资委网站和《人民日报》上。文章指出,推进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必须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方向,重要的企业由国有资本控股。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这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于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
文章说,由于国有大企业资产总量较大,管理层自有和可以规范筹集的资金难以或无法达到控股所需资金的数额,脱离实际情况推行管理层收购,难以避免不规范的融资行为发生,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 国资委新闻处官员表示,国资委研究室这篇文章代表国资委的态度。
这里也有两层意思,一是MBO歇了,尤其是大企业;二是文章先发在网站上而非媒体上,官员也学会利用网络这个准媒体来表达自己不成熟的态度。 不成熟的还有倪润峰和赵新先,他们都渴望改制,可以称之为“新59岁现象”:改制前,企业经营者的任免由上级决定,形同国家公务员,只要到点必须退休。而改制后,哪怕改成混合所有制,经营者的任免就由出资人决定,董事会说了算,市场说了算,就能延长权利的寿命。
辛辛苦苦一辈子,到老生出二心,这算怎么回事? 国资委话很少,但底下还是有动作。10月中旬,国资委、财政部、监察部和工商总局组成的国企产权转让联合调查组抵达江苏、浙江等省,对一些重大企业国有股权转让进行抽查。
人们很容易把国资委的动作与郎咸平联系起来。但国资委研究中心官员称:“国资委最近的检查工作,与郎咸平掀起的讨论无关。” 有评论说,为什么“有关”却要说成是“无关”?这里面不排除有害怕担责的因素。清查与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应当是国资委的职责,现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国资委而是由民间揭出来,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岂不是反衬出国资委工作不力,至少是不及时?此外,国资委也透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官本位心态,若承认是因为“民”言而采取行动,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
官员一定知道鲁迅的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欢喜得如此脆弱 思考过去思考未来
《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心情一定不爽,他说,当一个在中国台湾出生、在中国香港执教的明星教授戏剧性地高调挑起争论时,我们才发现我们社会过去20年赖以发展的共识,原来是这么脆弱。20年来,政府和企业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发展同盟。政府把资源向企业家集中,企业家得到一个中国过去前所未有的机遇发挥自己的天赋。二者合力,企业、经济搞上去了,企业家得到了中国社会以前不可能给予商人的社会荣誉,政府作为股东获得税利,皆大欢喜。
但欢喜得如此脆弱这应该是2004年的时尚用语一个学者几句话就能打翻这共同的欢喜。
一位居住海外的草庵居士话语尖刻。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痛,所以尖刻。他在网上说:郎咸平与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争论,更显示了中国人特别是精英们的弱智,在我看来,郎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私有化,在什么条件下私有化的问题,而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回答跑题不说,简直是驴头不对马嘴,干脆讲到中国正在否定私有制问题。私有化和私有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怎么就看不懂郎先生用中文表达的思想呢?难道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真的如此弱智?
这场争论谁是获益者?应该是郎咸平。但巧的是,郎咸平炮轰了TCL,而8月,TCL把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聘为独立董事,而郎咸平又在长江商学院当教授郎先生不怕项兵院长修理他吗? 好像不怕。
郎咸平说,从来没有企业花钱收买我。我的研究都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赞助的,我在长江商学院只是上课,也没有企业利益牵扯。企业通常都是抹黑我、丑化我、诬告我,这是它们一贯的做法,这也是我比较倒霉的地方。我所有的案例都是自己花钱做的,从没有得到过别人的支持。
郎咸平说:我今年48岁了,我简直不能想象当一个企业的顾问,可能两三年前我是愿意的,谁不爱钱呢,那时候我不出名。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了教父了,我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这就是一个人境界的提高。我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只需要你的财务报表,我就能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到的,就凭这一点,我足以称为教父。我是不是该谦虚一下?
郎咸平说:进而治国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我独善其身40多年了,已经够了!我举个例子,我在2000年时还默默无名,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就跟明星一样。我很喜欢做明星的感觉。
不能以郎咸平的境界来要求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境界是什么不好说,但可以从艺术家那里做个比较。 有
几个法国画家在北京逛了几天,他们有许多不明白,问咱画家:你开雪铁龙,画画能赚这么多钱?在北京东面的798废弃厂区转悠,问这么大的画室(整个一大厂房)几个画家用?在他们眼里,艺术家就是受穷的,虽然也有个把富的,但那与他们的主观追求没有关系,是身外附加的,艺术家就是追求艺术,贫富是别人的事。
其实,中国人也可以给他们讲几个中国艺术家,比如李叔同。李最早在中国提倡话剧,最早画油画,最早研究西洋音乐,“长亭外,古道外,芳草碧连天……”1918年,李叔同39岁时出家,抛掉“教父”的羁绊,号弘一,震惊了当时的知识界。人有三个境界,物质的、精神的、灵魂的,李叔同应该说达到这最高境界了。
但今天,咱跟法国人讲咱中国哪个艺术家达到了这么高的境界?如果问李叔同,他一定会接着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如果这法国画家换成经济学家,人家还会问:你们经济学家怎么能挣这么多钱?怎么还有官做有薪水拿有企业追着?
一个中国台湾人,不远千里从美国来到中国香港,又闯入内地,以正统“共产党员”的姿态掀起一场多年未见的争论。 这场争论过去15年了,参与争论的各位过得还好吗?是否还坚持自己当年的道理?是否认同最高院的22000字的判决书? 是否还有胆量、有热情、有新的道理再来一次大辩论?
《天下公司》是《证券市场周刊》旗下新媒体产品,主要关注上市公司经营、财务、管理、交易、法务等各类公告及相关信息。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天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