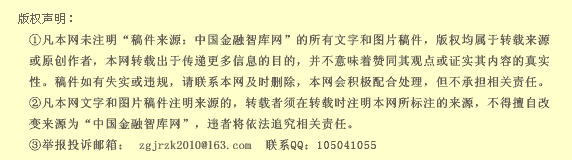没有市场,技术一定枯萎。
王牧笛:在中国人的历史中,“超级工程”始终是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修筑了万里长城、挖通了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和最长的跨海大桥。实际上,每当我们踌躇满志,对这些举世无双的“超级工程”进行审视和深思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是中国?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郎咸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是市场规模决定的。
举个例子,当我们问:“为什么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强权?”很多人的回答可能是因为美元霸权,或者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创新等等,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结果。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强权,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1900年开始的将近120年的时间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逻辑是这么来的:当美国成为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之后,想要赚钱的人就得和美国人做生意,自然就会接受美元结算,所以即使70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的时候,人们还是愿意使用美元。但是当所有国家都持有美元外汇的时候,美国人又通过外国人投资审核委员会来限制外资收购美国企业,这样美元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国出口的商品。美国政府通过低息的国债回收美元之后,通过国家意志来推动科技的发展。技术实现长足进步之后,再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来巩固这个优势。

但是现在,全球消费市场的重心正在悄悄发生转移。《华盛顿邮报》的数据显示,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消费市场规模是中国的7倍,但到了2018年,两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就已经差不多了,到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是9.779万亿人民币,美国是9.598万亿人民币,中国反超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你所说的各种超级工程,必定要依赖这个庞大的市场,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王牧笛:也就是说您认为市场比技术更重要。
郎咸平:这是一定的,没有市场,技术一定枯萎。比如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发展高速铁路网,这个技术欧美、日本也同样可以做,但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单一消费市场。
闫肖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国家意志和动员能力。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加拿大,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最近加拿大在争论一个事情,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石油要输送到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结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给石油管道项目施加阻力,特别是其中还牵扯到了政党斗争,这事儿就一直没能谈下来,结果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全加拿大、甚至可能是全北美油价最高的地方。这事儿要在中国,一个小组工作会议就解决问题了,这就是国家的动员能力。

王牧笛:当年邓小平同志访日,邓公坐上了日本新干线,然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速度很快,有催人奋进的意识。如果从今天看过去,当下的技术才真是天天催人奋进。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芯片这种高精尖技术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一手发展市场,一手通过国家力量来重新组织资源。
郎咸平:一样的。和上天入地、开山下海都是一个道理,市场是最基础的。
王牧笛:这个模式之前也有人讨论过,林毅夫先生把他称为“有为政府模式”,认为这样配置资源便捷而且高效,北大的周黎安教授称之为“晋升竞标赛模式”,就是说官员的晋升压力会激励地方政府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
闫肖锋:但是这个问题也必须两面看,政府作为组织者来动员大家一起干,这当然没问题,但是政府必须当好这个裁判,它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里根政府时期,当时美国政府大量向市场购买技术服务,但是它在购买的过程中仍然鼓励竞争。换句话说,我可以给你订单、给你补贴、给你好的营商环境,但最后还是要企业来唱这出戏。如果政府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个就容易出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惨痛的教训的,特别是新能源行业。

王牧笛:到也未必全是如此,我认为应该看领域,在一些充分竞争的领域当然可以,但是像一些修桥铺路,发展交通网这样的大工程,从技术难度到资金投入都是很多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
郎咸平:我给你做个补充。现在很多人在批评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实像美国的公司,在某些方面也有“国有”的属性,如果企业间搞一个行业联盟,那企业必须加入,再比如这次实体名单制裁华为,很多企业就只能照做,另外刚才谈到,有国外公司想要收购本国企业,很多时候是不被允许的。你不是号称自由市场经济吗?你这样做还是自由市场吗?
闫肖锋:从这方面来看,当然很多欧美企业都“国有化”了,反而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多内部治理都是不错的。
王牧笛:所以技术的红利、创新的红利,说到底还是市场和体制的红利。有个中国问题专家叫弗兰克泽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人对于西方技术的依赖在降低,而且每天在降低,而西方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却没有减少,每天在增加。”所以大众汽车的总裁最近说到了点子上了,他说大众汽车的未来取决于中国。
闫肖锋:而且你看西方的车企现在越来越多选择在中国搞首发。
郎咸平:原因只有一个。
闫肖锋: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嘛。